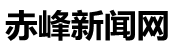本篇文章3555字,读完约9分钟
参观者正在参观纪念馆的阮忠/摄影
纪念馆外雕刻阮忠/摄
文件墙阮忠/摄
原标题: 90后南京大屠杀
□每12秒,水滴从高度空落下,落到黑色的“水面”。 这意味着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在那6周的惨祸中,每12秒就失去了生命。
□多个参观者在夏淑琴的“家”外,隔着窗户默默地擦去眼泪。 “至少在那一刻,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教科书上冰冷的30万数字,每个人都在那场惨祸中遭遇了”。 袁志秀说。
□我不是“和平时期的笨蛋”吗? 除了满腔怨恨和冰冷的30万,我对战争了解多少?
--------------------------------------------- -32 --------------------------------------------- -32
我决定去“熟悉不知道”的地方看看。 侵略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
引起这次访问的是微博。 北京时间4月15日凌晨,日本熊本县发生里氏6.2级地震,在网上受到嘲笑,纪念馆当晚意外地发出了祈祷微博。
“侵略战争时,熊本人组建的日军第六师团和第一零六师团都是侵略的主力,其中第六师团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 今晚,我们想告诉你日本熊本县日中友好协会的故事。 他们20多年来每年来我们馆吊唁遇难的南京同胞……现在我们很担心日中友好协会的朋友们。 你们好吗?
其实,这个选题在我接手之前,搁置了一个多月。 信息翻修的速度太快,我差点忘了这个微博时,又出现了男性领导人象征性的高亢声音。 “我听说来纪念馆参观的外国人中,最多的是日本人。
被心弦打动,感觉接触到了与“用手撕鬼子”“金陵十三钗”“浑身是血乱射”不同的历史。
在去南京的高铁上,在文科高中学习了3年,在文化产业学部学习了4年的我,拼命调动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但发现空空摇摇晃晃。
四个多小时过去了,脑子里还是只有一个冰冷的数字——30万。
“12秒”和30万人
进入纪念馆之前,我一直在想: 30万人是什么概念?
30万人可能是把地铁车辆做成沙丁鱼罐头的上班族,或者是当年和自己“争夺”全省5000名名额的四川老乡。
没想到这个数字会以墙的形式出现。
那是一面高12.13米,长20.08米的文件夹墙,踮起脚尖也大致只能接触到第二排的位置。 满满的文件装满了黑色文件的墙壁,拿起写着名字、年龄、家人状况、死亡经过等的书打开了。
足以挡住这个人视线的墙上有一万多件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和幸存者的资料。 看完这一切至少需要一个月。
纪念馆保管研究处的袁志秀副处长说:“与30万个数字相比,展示所有的资料还不够。” 文件夹的墙壁从地下1层一直插入到地上1层,即使支撑着整个墙壁,也只能放置1万人以上的资料,死者的资料也在增加,无法展示。
来自以色列的多个参观者在这里呆了很久,不想离开。 他们几乎没有懂中文的人,但是抚摸哪张白纸的黑字,眼泪就会一下子流下来。 因为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也有这样的档案墙。
纪念馆的研究者卢扬名访问过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馆内玻璃地板下放着成百上千双鞋,鞋的尺寸和形状各不相同。 唯一,他们是从灭绝营的一堆尸体中挖出来的。
在咚咚、咚咚、拥挤的纪念馆里,水滴落下的声音非常清晰。 在占地10万平方米的纪念馆一角,每12秒水滴就从高度空落下,落在黑色的“水面”上。 墙上点亮了印有死者遗像的灯,安静的蓝光消失了。
这样,循环往复。 五官不同,年龄不同的脸陆续点亮,与黑色墙面一体化。
说到南京大屠杀,大家都知道有30万受害者,但在那持续6周的大灾难中,以秒计算,每12秒就几乎不会有生命消失。 这是《12秒》的设计初衷,“让30万牺牲者的境遇回到每个人的境遇”。
那一刻,30万那么具体,又那么心痛。
我在“12秒”前站了几分钟,脑子里一直是自己做的各种计划,20岁当记者,30岁周游世界,40岁关注养生,生命不像炮火一样脆弱,好像有78十年的绵长。
来自美国的老虎队的儿子麦当劳站在这里,闭上眼睛静静地听了两分钟以上的水滴声后,在这些声音中,他说:“他目睹了父亲对中国人遭受了什么样的痛苦。”
三十万人都是家族的灾难。
在陈列室地下一楼的狭窄空之间,我不能太忽视那排矮平房。 隔着窗户一看,卧室里已经躺着几个“死了”的大人,隔壁房间,两个少女满是蓬头垢面,脸上全是黑色的污垢,她们蜷缩着,小心地舀着留在家里的锅。
这是南京大屠杀时幸存者夏淑琴和妹妹的真正经历。 在室外屏幕上,今年80多岁的她依然多次谈论自己的经历。
多个参观者在夏淑琴的“家”外,隔着窗户默默地擦去眼泪。 “至少在那一刻,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教科书上冰冷的30万数字,每个人都在那场惨祸中遭遇了”。 袁志秀说。
要表现战争的残忍,不一定要用血腥的场面。 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在《安妮日记》的黑白照片中,安妮双手重叠放在桌子上,弯下嘴角,露出少女青涩的笑容,“比起血腥的场面,这样的笑容更痛苦”。 卢彦名说。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玻璃墙橱柜里没有看到血腥的照片和影像,但到处都是数不清的首饰和眼镜。 都是从集中营带回来的,器物的主人无法知道年龄、性别、成长环境,唯一已知的标签是“死了”。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的黑暗甬道上,我本打算继续前进,但差一点就踉跄了。 仔细一看,发现地面凹凸不平。 解说员许晶晶告诉我,不平坦的道路也是设计这个会场的理念之一。 因为当时,关于战争的一切,“被压制和锁定”。
“这些票据是谁的? ”。
在展厅起伏的空之间,纪念馆把有限的一部分空之间留给了追求和平的日本人。
日本女教师松冈环因日本教材缺乏南京大屠杀,自费来纪念馆参观。 这里看到的“另一场”战争促使大屠杀幸存者和施暴者接受采访。
在《第十六师团第三十三步兵连队第一机枪中队战记》中,她给每个人打电话给上面的日本兵,如果对方还健在,就马上出发去采访了。
“你不是日本人! ”“南京大屠杀不存在! ”被拒付门前费是常见事件,这个身高不到1米6的小学教师一度被拒绝,再次背着照相机和录音机出发了。 她说她应该在两天内接到日本右翼势力的130多个恐吓电话,向学校分发传单,收中国人的钱被开除。
青年摄影师宫田幸太郎瞒着爸爸去南京拍了6次幸存者的照片。 在日本举行的摄影展上,日本右翼媒体激烈地提问:“我说没有南京大屠杀,怎么做这样的摄影展呢?”
这几年来,来纪念馆的日本人很多,出版的书籍和举办的展览会也不少,但纪念馆的日语翻译芦鹏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日本老人们举办的漫画展吗?
那个展览会被称为“日本100名漫画家回忆停战日”,展出的漫画来自一群漫画家,回忆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之日”的自己的所见所闻。
在团队出发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日本右翼媒体疯狂攻击召集者石川好,说:“日本人的伤心如何能在南京人面前展示呢? ”。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展出这些漫画。 你有这样的心情吗? ”。 石川经常回答的声音在颤抖,但声音是“坚定有力”。
一位白发漫画家认为他们很多人“中国人不会原谅自己”,这些老人说“去中国好几次”,腰缠着白带准备“以死谢罪”。
我以为错误的地面会把我彻底导向悲伤和仇恨。 就像过去十几年,就像我受过的教育一样——说南京大屠杀这五个词,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血腥的屠杀场景。
在纪念馆的某个地方,给我看了战争的“另一边”。 那是战后几十年一时的日本人的行动,有“看起来轻重不一”的历史细节。
例如,那一面记录着数百手指纹的墙壁。 在红沟里,什么样的老票据变形得像鸡爪,有些纤细瘦弱的就像幼儿的手,这是纪念馆员工在全国几十个省跑后采集的抗战胜利的退役军人票据。
我试图把手伸进去触摸,但两者都变形了,找到了老化的手,几乎没有人能把手伸进我这个有点婴儿的胖手。
的解说员说,退伍军人的遗属多次抚摸票据,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哭得像孩子一样。
然后,孩子们对爸爸说:“这些票据是谁的? ”。
年轻的父亲抱着孩子时,父子的手重叠着抚摸票据,“你知道吗? 他们用他们的手赶走了侵略者”
好几代人都在这个历史时刻重合,就像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画面一样。 在游行队伍中,穿着前苏联绿色军服的退役军人走在最前面,他们头发变白,拄着拐杖。
跟在后面的是年轻的俄罗斯人。 他们是退伍军人的遗属,父辈已经破损身着白色衣服,父辈的遗像抱在怀里。 广场上响起了手风琴的声音。
在纪念那场胜利的日子里,这似乎是更安静的警告。
“我们是胜者,也是受害者。 显示战争的代价不是为了点燃仇恨,而是为了提醒人们带来和平不容易,不要引起战争。 ”。 纪念馆的一位员工说。
那一刻,战争不再是我脑海中的坚船利炮的对抗,也不再是血海深仇大恨的愤怒,我对它的理解更多,更多,越来越多样。
1 2 3 下一页 1 2 3 下一页标题:“一名90后眼里的南京大屠杀:"12秒"与30万人”
地址:http://www.cfcp-wto.org/cfzx/194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