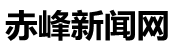本篇文章6916字,读完约17分钟
4月13日,俄罗斯电视台2频道(正式名称为“俄罗斯1台”)将在艾戈尔·阿纳什金导演、鞑靼族女演员丘吉尔·潘·哈马特巴主演的黄金档播出。 电视剧根据鞑靼女作家古泽丽雅辛娜( guzel yakhina )于年出版的同名历史长篇小说改编。 这是雅西娜的长篇处女作,意外地获得了俄罗斯最重要的年度文学奖“大书奖”和其他系列同样重要的奖项,被翻译成了简体中文(人民文学出版社于年出版,译者包括张杰、谢云才)在内的十多种语言。 《祖列依哈睁开眼睛》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农村集团化运动中的苏联为背景。 (警告:剧情透支! 不会读写的鞑靼农妇的祖先雷·哈瓦列娃住在父亲制度的家庭里,受到丈夫和婆婆的虐待。 她和丈夫在藏粮食的途中被征兵队撞死,队长伊万·伊格纳托夫被杀,兹雷哈作为“富农婆”被剥夺财产,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 在坚强的意志和困难的伙伴们的帮助下,祖先伊哈在地狱般的流放路程和流放地的第一个冬天,生下了穆尔塔扎的遗子尤素夫。 虽然在流放地的生活非常痛苦,但祖先伊哈得到了新生。 被流放的知识分子和前贵族很重视母女,把尤塞夫培养成了有潜力的画家。 护送队伍的伊格纳托夫现在是流放地的警卫队长,和祖先雷哈渐渐有了感情,两人终于一起去了。 成为良心未泯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他不想捏造假案枪毙居民代替职业生涯,激怒了上司。 解雇前,伪造优素福的出生说明,登记为儿子约瑟夫,促使他走上圣彼得堡的绘画之路……(剧透结束)在“反苏”“辱露”一词下,历史的再迷思化根据被称为的历史小说进行了改编。 疫情封锁期间所有人在家看电视的时机——这是阿纳什金这样的年轻导演出名的绝佳契机,但当第一集播出时,事件的迅速发展是所有人都预料到的:社会交往媒体和电影评价网站翻山越海 更阴险的是,很多谩骂绕过了电影的真正负责人,针对了两位女性原著作者雅辛娜和女主角哈马特娃。 脸谱上的顾客帖子,“俄罗斯的一台播放了连续剧《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 女辱露分子丘比特·潘哈马特娃在这部反苏推广电影中担任主角。 美国国务院订制了这部电影,我们俄罗斯一台转播了它。 丘比特·潘哈马特娃是柿子油党( liberast ),一边参加lgbt运动,一边舍不得攻击苏联法西斯。 这次封锁只是起到了负面作用,正如作家沃德·拉兹金所说,俄罗斯人只是“喝150克就睡觉”,早上开始再去一次班。 “骂某人,踢桌子泄愤,然后就可以了。 但现在没有类似的宣传渠道。 他坐在家里,会骂的人已经骂过了。 有一部电影上映了,拿出电脑和手机开始发消息。 “被电影的角度左右而成为‘友尽’的例子也相继出现,文学评论家加琳娜·约瑟夫维奇说:“把6个朋友关起来,把其中2个人拖成了黑色。” 政治家很快就闻到了擦热点的机会 擅长商讨名人著称的非主流小党“kpkr”的党首斯莱金( maksim suraikin )系着他标志性的打牌领带,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形式的领导剪辑中发表声明,将电视剧称为“新闻战的构成要素” 此外,主流kprf议员加夫里洛夫( sergei gavrilov )要求检察院审查电影副本,要求文化部停止支持这种“抹杀国家历史、分裂社会、侮辱信徒”的电影。 讽刺的是,让检察官调查文艺作品的议员是议会“公民社会快速发展委员会”的负责人。 “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的粗话的理由,只不过是以农业集团化时期残酷的脱富农化运动( dekulakization )为背景的故事。 “苏联取得了这么多辉煌的成果,没有拍摄卫国战争、宇宙竞争、大国建设,而是盯着这些黑暗面拍摄,这不是抹杀吗? 》背后的深层逻辑其实是新世纪是俄罗斯社会主流舆论对历史的再迷思化,这种再迷思化扭曲了苏联从1980年代末开始对历史进行迷思化的过程,但新时期的历史迷思与苏联时代不同:对后者来说,迷思化的历史是自身 不管是哪个大国,俄罗斯帝国还是苏联,这完全无关,只要国家足够大就行。 并不稀奇,3年前的人畜无害电影《马蒂尔达》( matilda )因为讲述了末代皇帝的婚外史,被同样热爱瓷器的君主主义者们贴上了“辱露”的标签而受到批评。 两部电影的攻击者看起来在政治光谱的两端,但他们有大致相同的想法,为同一个体在议会中充当橡皮图章,被他们动员参与集体迫害的可能也是同一集团。 根据这个逻辑,也可以大致理解现代俄罗斯主流舆论“降格崇斯”的倾向。 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对这种思潮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前大国被列宁“摧毁”。 斯大林重建了大国。 当然,这给电影导演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例如,如果在俄罗斯内战拍摄时丑化白军,美化红军,他可能会受到侮辱,但如果否定描绘斯大林上位的红军,依然会受到侮辱。 但是5年前,《祖列依哈》的小说问世时,得到了普遍的评价,只有作者的故乡鞑靼斯坦受到了批评(详见后述)。 那为什么电视剧播出后受到完全不同的对待呢? 这是因为在现在的俄罗斯,电视和书籍的受众是完全不同的两组。 1999年以后,俄罗斯电视节目,特别是复盖全国的几个“联邦频道”被官方强力限制,这一限制在年克里米亚事件后进一步加强。 电视节目中充满了假情报和阴谋论政治脱口秀,人们现在经常用“僵尸盒”( zomboiashchik )嘲笑电视。 比较不夹紧的图书市场多少有些体面。 结果,就像苏联摇滚元老和时光机乐队( mashina vremeni )的灵魂人物马卡列维奇( andrei makarevich )有点刻薄地评论过的那样,“书在说别的吗,电影在说别的吗? 不是那样的 书是一本好书,电影不好吗? 也不是。 ……不仅我们的国民被整整齐齐地分成两个物种 一个物种可以读书 另一个看电视 ……这六年来我一直在勉强育种。 我们刚开始收获果实。 但是,讽刺的是,制作这部电视剧的俄罗斯一部书应该是“僵尸箱”最积极的育种家,轻而易举地知道如何操作“僵尸”。 再者,为了照顾电视观众的心情,电影在拍摄时悄悄地磨练和粉饰了原著的各种尖锐之处,结果得罪了所有人。 另一位著名作家维克多·埃罗菲夫的评论说:“两个频道很幼稚,毕竟斯大林的所有成果都不肯定,认为可以集体化……成为开放的话题。 不,现在不可能! ……政府的头领们追不上了,现在民众……走得太远了。 我们再次是悖论。 国家脸上的人物……比充满仇恨地批判这部集体化主题素材电影的大众更自由派。 所以,连年后过于接近当局,不惜亲自去东乌克兰战场的人气作家普里平( zakhar prilepin )也意外地表示了对雅辛那的支持。 但是,这种表现的动机与其说是对同行的称赞(毕竟他承认自己没有读过原著),不如说是害怕——因为即使是他这样的受当局欢迎的人,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僵尸”后浪的下一个席卷对象。 o tempora! o mores! 几乎十年前,俄罗斯的一台拍摄了比《祖列依哈》暴露性高得多的文学改编剧索尔珍妮·双人的《第一周》( v kruge pervom )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 zhizn i sudba ),全部获得。 但是,也有不投降的勇者,这次受到最严重打击的哈马特瓦就是其中之一。 她不谦虚的公开反应再次使我感受到这位优秀演员的智慧和人格魅力:这种狂暴的反应越来越多使我吃惊。 为了知道我们的电影只是斯大林时代实际发生的事件的非常轻快的版本,我担心大家会因为不够敏锐而批评我们。 我认为冲洗过去的基础是幼稚、无学、惰性。 我不想泡在那里。 但是,需要知道的文学索里尼、萨拉莫夫、格罗斯曼和戈伦斯坦并没有消失。 只是读它需要内在的努力 现在不学无术、无知无畏的人多了 操作这些人不太复杂,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们很方便。 他们把历史的悲剧标志看作是个人的屈辱 我向孩子们指出错误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反应的。 ……还记得《艾伯特的孩子》播出后人们的反应。 “我们厌倦了你们和你们的斯大林! 够了! 你们不用说我们也知道全部。 但是,实际上斯大林化在社会上最终也没有发生。 原因没有勾画出来,事实没有说清楚,没有得出结论。 一切就这样继续下去 尽管有这样的病态反应,我们认为有必要积极地遵守自己的注意、自己的观点。 社会必须意识到去富农化是犯罪,是杀人,是无数人的悲剧。 这是改变我国历史的道德伦理灾难 至少不要陷入记忆丧失 一部电影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触这个问题取决于各自的导演自己。 我认为这种迫害不是和我的个人相比的。 宁可我们的社会完全没有做好自我教育的准备,也在开拓关于自己的真相。 人们允许自己用这种敌意或蛮横的口气攻取别人的“肮脏历史”,其中有某种规律性。 一切都混在一起,互相关联。 例如,粗鲁相关的是野蛮和敌意。 选择合适的语言无法描绘自己的心情,只需要吐口水就可以离开。 他们没有意识到不需要浪费时间来伤害别人。 但我认为敌意也是防御机构,包括防御恐惧。 现在很多人都害怕了 鞑靼族炮火:东方主义殖民文学? 但是,除了斯大林主义者的猛攻,《祖列依哈》是从另一个方向受到炮火的作家和女主角的故乡,也是故事的发生地鞑靼斯坦。 在电影中,鞑靼族的角色都被指责说流利的俄语,服装、道具、舞美被指责不是民族学风格。 祖列依哈最后和杀丈夫的敌人俄罗斯人伊格纳托夫一起去了(“我们鞑靼女人决不会这么做! ”,优素福的名字俄罗斯化,被伊格纳托夫的父亲称为姓,被认为是在背叛民族以前流传的。 残酷的穆尔塔扎和“吸血鬼”婆婆的描写被认为是丑陋的鞑靼人以前的传人生活……伊斯兰教界也强烈不满。 因为在清真寺的布尔什维克2人的激情剧、流放者出发前被提名的名单中,也包括现实中存在的鞑靼教界名人、以及现俄罗斯最高穆赫蒂(逊尼派的神职人员)。 另一方面,在鞑靼民族大会( milli medzhilis )、鞑靼老年人委员会( shura aksakalov )、全鞑靼公共中心( vtots )三个民族组织的联合声明中,雅西娜和哈马托娃都“排斥鞑靼国籍” 鞑靼语和鞑靼精神都不一样 “和斯大林主义者一样,鞑靼人的批评者也把矛头指向公共机构,制作电影的俄罗斯之一是被称为莫斯科丑化鞑靼人意图的传声筒,鞑靼人和喀山地方当局慷慨赞助电影拍摄的行为背叛了民族利益,恶意的 古泽丽·雅辛纳预计小说问世后会有很多类似批评,因此在连续剧播出后会有类似的声音,但在鞑靼斯坦相信支持她的意见是主流,但只不过是“恶意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时大”。 然后,雅辛娜说这本小说有两个层次。 鞑靼民族的身份,苏联的历史背景只是表面。 她真正表现的是超越民族的层面,“是一个女性从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的位移,这种空间转换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史学家伊丽娜·谢尔巴科娃认为鞑靼市民的反对浪潮有“逆向思考化”的倾向。 为了对抗苏联政权创造的历史迷思,他们创造了反叙事诗,戴着玫瑰色的眼镜注意苏联政权到来前的农村生活、民族以前的传入和父权制秩序。 来自鞑靼斯坦的批判性发言,反而有理由认为雅辛纳在小说中描绘的父权制思维模式并没有真正离开这片土地。 例如,历史小说家伊马莫夫( vakhit imamov )说,这本小说不是雅西娜一个人完成的,尤其是关于在流放地建造土窑的片段。 “要知道制作窑的所有细节,首先必须熟悉这一行。 只有男人知道这个。 没有一个女人知道建造土窑的细节 这是男人为她写的 女性在这方面没有智慧,也没有必要拥有。 但是,鞑靼人的声音不是肤浅和无理的骚动。 例如,鞑靼族德语文学研究者努里阿·法特霍巴在柯尔塔内特( colta.ru )上刊登的批评副本《兹列耶哈反祖先里耶哈》( zuleikha protiv zuleikhi )。 小说中,除了苏莱哈以外,几乎所有的鞑靼角色都被描写为负面角色,但接受苏莱哈的“再生”、“开眼”、“现代文明”是随着宗教信仰(既有伊斯兰教,也有多神教)和民族传来的放弃,这种女性主体 尤素夫的改名是伪装成现代化的俄罗斯化故事的壮丽结束,这使我想起斯大林时代强迫少数民族大规模改变俄罗斯族名字的实践。 小说的情节结构很符合古典东方主义殖民文学的道路:俄罗斯人(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受迫害的旧贵族和知识分子)表现为西方/文明的化身,鞑靼人是东方/野蛮的他人。 男性作为危险主体被杀害,消极的女性被征服者(伊格纳托夫)作为战利品带走,带入西方主体的规范空间,服从“进步”的力量。 无论是对苏联式女性解放的赞美,还是塑造人物时的有点刻板印象的方法,雅辛娜的小说都沿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向,忠实于东方主义殖民地文学,这一点从以前就流传下来了。 这是现代着名作家乌里茨凯亚在小说中写的序言,难怪使用雅西娜和伊斯坎德尔( fazil iskander )、莱特海奥( yurii retkheu )、阿特马托夫( ching )。 但是,很多鞑靼批判者担心的是:“根据粗糙的风格化描绘的鞑靼文化形象来赞扬俄罗斯化,原著表现为民族文学的新典范。” 所以小说和电视剧化都可能受到俄罗斯官方媒体和文化建设的支持。 因为硬币的表面是“多民族和谐共存”,背面是前提条件——曝光。 尽管帝国遗产正在枯竭,帝国的语言依然统治着俄罗斯的舆论场,即使是以前流传下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不是超然的。 在围绕“祖列依哈”的争论中,自由派认真批判和解体了斯大林主义者的发言。 对鞑靼斯坦的反对几乎是模棱两可的,只有“鞑靼民族主义者也感到不满”这句话,上述作家埃罗耶夫才放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首位。 事实上,在现代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称呼根据语境有完全不同的内涵。 另一方面,公然持有法西斯主义和新纳粹立场的俄罗斯人被舆论婉转地称为“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只要表现出一点自觉的民族意识,就马上被贴上“民族主义者”的标签,作为潜在的极端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受到批判。 法国谚语“削俄罗斯人就能找到鞑靼人”众所周知,莫斯科和喀山很高兴推广“鞑靼人是模范的少数民族”,“鞑靼人是与俄罗斯人最和谐地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 在欧亚草原上从东到西波涛汹涌的游牧民族一直被认为是来自俄罗斯人东方的其他人,金帐汗国长达2半个世纪的统治在俄语中被称为“蒙古鞑靼束缚”( mongolo-tatarskoe igo )。 在鞑靼人的自我认识中,他们已经在伏尔加河流域定居的保加尔人( bulgars )之后,“蒙古鞑靼束缚”实际上是“蒙古束缚”,他们自己也是金帐汗国统治的受害者——这是“祖列依哈”中,鞑靼人 无论是俄罗斯普通市民还是很多知识分子的认识,鞑靼人都与从东方来焚烧掠夺的牧民的形象紧密相连。 就像塔科夫斯基( andrei tarkovskii )的电影《安德烈·布里奥夫》( andrei rubliov )。 然后今年4月初,普京在抵抗新冠引起的肺炎的第一次国民演说中,与曾经“拷问”俄罗斯的东方游牧民族进行了病毒比较,但考虑到现在政治的正确性,并没有提名鞑靼人,而是被鲜为人知的佩奇能源人( Pechh 对鞑靼人来说,自从伊巴莱蒂1552年攻陷喀山以来,身份证危机一直如影随形。 俄罗斯人确实会带来西化和现代化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它,就必须抛弃民族宗教,以前流传下来,牺牲语言。 民族及其文化复兴的苗头总是被警惕的莫斯科马上掐死。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ismailgasprinskii ( ismailgasprinskii )新教育法扎扎德运动的开展,喀山曾经成为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但这项运动在俄罗斯国内 1992年,鞑靼斯坦通过全民投票和宪法制定进程实际宣布独立,但最终在莫斯科引起了狂澜,最终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了俄罗斯联邦。 鞑靼斯坦是以俄语和民族语为中小学必修科目的俄罗斯少数地区,这个“特权”也终于在莫斯科和当地俄罗斯人的持续攻势下结束了。 莫斯科在今年提出的宪法修正案中继续获胜,在俄语为俄罗斯联邦“国语”的第68条第1款中,现在增加了“构成国家(作为gosudarstvoobrazuiushchii,state- )”的非常顽固的补充 什么是“构成国家的民族”,为什么俄罗斯族能“构成国家”,鞑靼族不能“构成国家”是需要博学的宪法学者们进一步说明的,这个修订显然是鞑靼语越来越形式的地位 面对这样的持续压力,成为鞑靼人首先不是意味着谁,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韩国谢尼人,不是归信基督教的鞑靼人,或者是以各种形式俄罗斯化的人,面向防御性和否定性。 在没有中间道路的情况下,(后)殖民地时代的鞑靼知识分子依然面临着用俄语接受教育,成为雅西娜和哈马特瓦这样的俄罗斯化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困境(要建立一个不会失败的帝国,俄罗斯提供给少数民族的类似机会比较多 或者保护自己的身份承认和文化,对来自俄罗斯的新事物持自然的拒绝态度,越来越退缩到小众的语言空间,走出同温层就被视为“民族主义者”乃至“原教旨主义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围绕《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的小说和电视剧在鞑靼斯坦的争论,可以认为是以后殖民时代的鞑靼人,甚至殖民时代的弱小民族的身份承认焦虑的最新脚注。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
标题:热门:“小粉俄”与鞑靼族的双重讨伐:一部俄剧背后的历史迷思
地址:http://www.cfcp-wto.org/cfzx/17031.html